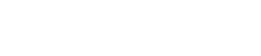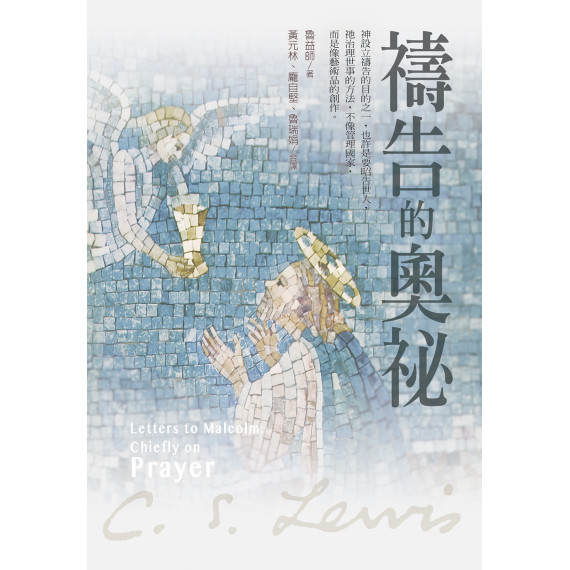禱告的奧祕
在禱告這件事上,神要我們成為藝術家、工程師,
而非只是初學者。
手機對現在的孩子可能是遊戲機,但在程式語言工程師眼中,手機卻是能改變人類未來的關鍵創意媒介——「禱告」或許也是這樣。
我們可能做了基督徒許多年,但對禱告的認識卻未同等程度的提升,對於如何禱告、禱告將碰到的狀況、禱告未蒙應允等情況大概熟悉,但似乎逐漸對禱告沒有更多感想與感受。禱告究竟還能給我們什麼?
魯益師寫過無數膾炙人口的作品:《痛苦的奧祕》、《小心魔鬼很聰明》、《納尼亞傳奇》等,最後卻決定寫「禱告」——這個簡單又艱難的主題。在《禱告的奧祕》中,魯益師和我們聊如何禱告、生命的高山與低谷,以及最終的盼望,以其淵博學識與喪偶的切身經歷,更深探討禱告究竟是什麼?如同手機,當我們對禱告的了解不只是如何操作,更是背後的程式語言運作模式時,就能讓禱告為人生開啟更多可能,在禱告中更深地揭露自己,享受與神面對面的時刻!
魯益師(1898-1963)
本持無神論,三十三歲成為基督徒,自稱是全英國最不情願的歸信者,後來卻成為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護教家。魯益師從小酷愛閱讀、涉獵廣博,文學涵養極為豐厚,也受過嚴格的蘇格拉底式哲學辯證訓練,但從未接受正式神學教育。
於牛津大學教授文學的魯益師,自一九四O年出版《痛苦的奧祕》等書以來,漸漸奠定在文壇上的地位。然而好景不常,骨癌卻帶走了他的妻子喬伊,重重打擊魯益師的生命,在傷痛中他匍匐走過,寫下了生前最後一本書《禱告的奧祕》。書中論及禱告卻沒有得著所求,他只淡淡地說:「但實在說,從整個屬靈生命來看,『蒙神記念、考慮』,實在比『得到所求』重要得多」。
01 公禱
02 現成或自想
03 環境
04 渴望
05 主禱文
06 宗教、自滿與罪咎
07 決定論
08 苦難
09 自由意志與恩典
10 目的
11 得不著
12 神祕經驗
13 誰在禱告
14 逃避
15 真我
16形像
17歡愉
18 懺悔
19聖餐
20死後
21不愛禱告
22復活
導讀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系統神學教授、
基督教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林鴻信
一九六三年三至四月間路易斯(C. S. Lewis)寫作他最後一本書《致馬爾肯書信集:論禱告》(Letters to Malcolm: Chiefly on Prayer),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去世,之後隔年出版此書,主題是「禱告」(中譯本書名為《禱告的奧祕》)。一九五二年路易斯出版《如此基督教》(Mere Christianity),曾經策畫過寫一本關於禱告的書,可是在兩年之後放棄了這個計畫。《禱告的奧祕》採用書信體裁,以二十二封寫給假想的馬爾肯的信來呈現禱告的主題,這使他在討論禱告時可以面對具體而真實的生活處境,並且讓他不必有居於權威地位發言的壓力,而可隨意分享、討論、發問與建議,並且不用發展出完整的禱告看法,這個特別的文學設計讓他有比較多靈活的空間來探討這一個艱深的題材。
然而,這畢竟是一本神學著作,而且是非常成功的神學著作,也是他生平最後一本著作,此書呈現傑克在喬伊去世之後的神學觀點,在歷經喬伊去世帶來的痛苦後談論禱告,這本身就是一個十分敏感的議題,讓我們有機會觀察他在歷經掙扎之後的思想發展,書中的主題仍然圍繞在他一貫追求的「真實」。值得注意的是,此書不再有過去他雄辯滔滔的護教風格,而是更接近娓娓道來的信仰告白,形式與內容都呈現出溫煦敦厚的特質,這應當是從他的人生成熟階段之智慧的自然流露而比較低調,路易斯精密推理、辯才無礙的特質逐漸地轉成誠懇地心對心之分享。
一、敬拜上帝
在神學上,聖公會高派傳統比較重視禮儀,因此比較接近天主教會;而聖公會低派傳統比較重視講道,因此比較接近宗教改革以來的基督教會。路易斯提醒我們說,上帝與我們的距離又近又遠,「我們應該(有時候希望我們真是如此)感受到祂與我們無比的親近,又同時意識到祂跟我們之間無限的距離。」正由於祂是全能的上帝,祂必定離我們無比親近;也正因為祂是創造者上帝,祂必定離我們無限遙遠。
路易斯對於禮拜具有創意與自由的精神,他提倡活潑而不重視形式的另外一面,比如他嘗試把經歷任何來自創造的美好之「每一刻的歡愉變成崇拜的管道」,他強調「『經歷這小小的神的顯現』本身就是崇拜」,而非在經歷歡愉之後才發出崇拜之感謝與讚美。在這方面,禮儀顯然並不是主要的,而是讓每一次生活中的感動都成為崇拜,而不是在體驗感動之後前往參與禮拜才是進入崇拜,乃是讓感謝讚美發生在日常生活當中。路易斯期盼,每一刻的歡愉都可以成為上帝顯現的經驗,這對於路易斯那個重視傳統的時代是不常見的主張。
二、如何禱告
路易斯在喬伊過世之後談論禱告,亦即在極力禱告之後不被應允,十分敏感。然而,書中十分平靜地指出,由於上帝已經知道一切,禱告裡的「認罪」只是在「告訴神一些祂比我們還清楚的事情」,禱告裡的「祈求」自然也不過是「告知」並「索求神的注意」而已。
1. 揭開自己
那麼,究竟為什麼對一位已經知道一切的上帝還要禱告呢?禱告的真正功用在於「我們揭開了自己。……改變的是我們;被動地,轉成主動地被認識。不再是單單被知道,我們闡述、披露自己,我們呈現自己讓神察看。」重點在於,禱告是改變自己,而非改變上帝;禱告是人對上帝主動傾心吐意,而非人等著上帝明白人的想法。
2. 真我與真祢
作這樣的禱告,最重要的態度是「真實」,「在上帝面前我們必須說出『我們所想的』,而不是『我們應該想的』。」「我們所想的」才是我們真正的樣子,「我們應該想的」常常只是我們自己認為我們應該有的樣子,或者別人認為我們應該有的樣子。一個失真的禱告,就像一些虛浮客套、行禮如儀的禮貌性談話,不會有實質溝通的效果。因此,「在所有禱告前的禱告應是:『但願說話的是那真我,但願聽我說話的是那真祢。』」。
路易斯一生經歷過最大的真實經驗就是與喬伊的婚姻所帶給他的,但真實的東西並不必然帶給人舒適的感覺,由於真實的有稜有角,也必然會讓我們在與真實會遇時經歷挫折,這些挫折其實對我們的成長有益。
路易斯從喬伊身上學習到的真實體驗,也可以應用在他與上帝的關係。這意味著,上帝若是真實的,祂既可能垂聽亦可能拒絕我們的禱告,這是路易斯在喪母之痛與喪妻之痛的過程裡,從禱告中所體驗到的。真實並不是一廂情願,既然追求真實,就應當在禱告中走出虛幻的世界,勇敢地向真實的上帝打開真實的自己。
3. 被上帝記念
既然禱告追求的是真實,那麼禱告是否得到應許就不能說是最重要的目標,因為真實包括真實地應允,自然也包括真實地拒絕。
「但實在說,從整個屬靈生命看來,『蒙神記念、考慮』實在比『得到所求』重要得多。」。「蒙神記念」確實比「得到所求」更有價值,路易斯在輕描淡寫當中已經回答了許多讀者的疑惑—究竟他是如何面對上帝並未垂聽他為所愛的人的禱告。從母親去世,到妻子去世,他究竟如何能夠堅定地繼續作一個基督徒呢?答案就在於「被上帝記念」。
4. 公禱
有時候禮拜中的公禱帶有太多術語,或者為了追求流暢而表現得比較「職業化」,令人覺得失真,好像是公式化或官方的宣讀。公禱的時間本是由一個人代表會眾禱告,如果公禱無法代表大家真實的心意,會使得與會者不知如何跟著禱告。公禱的「公」原本是指從信仰團體的角度出發的禱告,並不是說公禱一定要為世界大事禱告,然而這個「公」造成一種錯覺,似乎必須「大公無私地」為「公共事務」禱告,當過度勉強為公共大事來禱告時,那種禱告自然容易失真。公禱應當是為信仰團體有感動的事情來禱告,有可能是大事,但也有可能是小的事,若是出於真心感動,公禱就不會失真。
5. 代禱
路易斯提到,代禱的原則在於「先神後人」,「當我們專心向神,我們會自動想起需要代禱的人;但注意著人,卻不會自動想起神」。當人心向著上帝時,就會被提醒哪些人是需要為他們禱告的,從上帝來的感動導引著我們轉向人,這是一個很好的原則,代禱應該從面對上帝、敬拜上帝延伸而來。
追根究底來說,禱告畢竟完全是出於上帝本身,與其說人在禱告,不如說上帝在人裡面禱告。當我們深入地追問「究竟是誰在禱告」時,必定不敢輕易地說是我們自己在禱告,因為我們一切的禱告都是在上帝的帶領之下,我們不能忘記所有的禱告都是在上帝的主權之下,從禱告的負擔與動機到禱告的行動與內容,一直到禱告的後續關懷,都是上帝在帶領。
6. 圖像
路易斯主張在禱告時身體感官與心靈專注之間的密切關係,「視覺的專注可以象徵,且能提昇心靈的專注」。然而,過度使用感官圖像,反而可能成為禱告的絆腳石,這對心靈圖像而言也是如此。路易斯對於禱告時使用心靈圖像的態度是複雜的,一方面他認為過於寫實的心靈圖像幫助不大,另一方面心靈圖像卻在他的禱告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在稍縱即逝的片段中,是真實帶來的撞擊。顯然路易斯在積極支持感官圖像與心靈圖像的同時,小心翼翼地想要避免狂熱和偶像化的危險。
7. 為你或為我?
路易斯是一個觀察細膩的思想家,他看出許多禱告時的問題發生在人的一方,比如說,「有時候我們不為小事祈禱,是為了自己的尊嚴,不是為了神的尊嚴」。當我們不肯為一些小事禱告時,是不是因為我們太過於顧及自己的尊嚴呢?另外,當我們覺得面子受損或自尊心被傷害時,儘管也不是什麼大事,我們卻可能在禱告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會不會是問題出在高舉自己的尊嚴呢?反過來說,當上帝的尊嚴受到侵犯的時候,我們真的會很在乎而全心全力禱告嗎?
進而言之,當我們說為了上帝的尊嚴而為「大事」禱告時,往往並不切身而淪為空泛不實,或許隱藏在為了上帝的尊嚴之下,竟是為了維護我們自己可憐的尊嚴吧!而且,當我們看輕「祈求的禱告」時,真正原因往往並非信仰成熟超越這些需求,而是出於缺乏信心,我們害怕自己的不信會被揭發出來,只敢嘗試那些信心不會受到考驗的禱告,在這裡面也隱藏著維護自己尊嚴的私心。
8. 邁向成熟
禱告的問題往往是出於人的問題,禱告恰當與否其實關連到人的成熟與否。「如果我們已臻至完全,禱告將不會是責任,而是欣然之樂。」英文的「責任」(duty)帶有外來要求的含義,對於尚未完全的人而言,禱告可能仍然是出於被動地受到要求的託付,而不是主動地自發性動作,遑論是一種享受。
然而,我們在被動中仍然要學習,直到禱告成為主動的享受。既然我們現今尚未完全,那麼禱告必定還是一種責任,我們不但要學習承當責任,也要學習成長,期盼有一天能夠更加成熟,不再把禱告視為責任,而是視為享受。
01 公禱
萬分同意你的想法。你向來主張我們的書信往來應有個「討論主題」。上次我們分別後,書信往來因為沒有主題而乏善可陳。大學時代的作法真好,那時我們以書信長篇大論地討論《理想國》、古典詩的韻律,以及當時新興的心理學。沒有一樣東西較比意見相左的辯論,更能使兩地相隔的朋友活現眼前。
你所建議的主題──禱告,常盤據我的思想。我指的是私禱。如果你想談公禱,恕我不能奉陪!除運動外,教會禮儀學是我最無話可說的課題。僅有的一點雜感,就此一次在這信中說完罷了。
禮拜儀式的變化
身為平信徒,我們應當接受教會所安排的禮拜方式,並且盡力善用之。但如果各教會在禮拜儀式上能恆常與一致的話,我們配合起來就容易得多了。
實際看來,持這樣看法的神職人員並不多。他們似乎相信,如果在禮儀上多有變化,例如變化多端的熄燈、點燭;這裡加長、那裡縮短;今天繁複、明天簡化,信徒們會更願意來教會。不錯,任何一位有熱忱的新牧師總能在自己的教區內,凝聚一小群喜歡這些新玩意的會眾。但恐怕大多數人對這些花樣不感興趣,很多索性脫離教會。留下的人,只有默然容忍。
大部分信徒無法接受新的改變,是因為墨守成規嗎?我想不是。他們如此保守,背後是有理由的。很多這些所謂的創新,其實只有娛樂價值。而信徒到教會,不是為娛樂。他們去,是去「使用」那場崇拜,或是(若你喜歡這樣說)去使崇拜「發生」。每一個崇拜,都是一系列言語和行動的組合,透過這些,我們領聖餐、悔改、代求,或向神傾訴敬慕之心。當我們不再需要注意「禮拜儀式」,也就是說,當我們對禮拜儀式很熟悉,根本不用去想它的時候,它就最能發揮崇拜的功效。若是還在留意腳步、刻意去數點步伐,就還不是在跳舞,乃是在學習跳舞而已。最好的鞋子,就是穿上後根本留意不到它存在的那一雙。不再留心眼力、光線、印刷、拼字時,我們才能享受閱讀之樂。完美的崇拜不會讓我們留意到崇拜禮儀,因為我們注意的完全是神。
每一種新東西都會打擾這種對神的專注。它引我們去注意崇拜的禮儀;如此「想著崇拜」跟「崇拜」當然是兩回事。問及傳說中的聖杯,最重要的問題是「它有何用處?」、「把服事看成比神明更重要,簡直是瘋狂的偶像膜拜」。
更壞的是,新東西可能不引導我們注意崇拜儀式,而吸引我們注意崇拜的司禮人員。你知道我的意思。雖然努力排除,但「究竟他又在玩什麼把戲?」這問題會不請自來,硬闖入我們的腦袋,把敬拜之心全然摧毀。難怪有人說:「但願他們記得,主交給彼得的命令是『餵養我的羊』,不是『以我的老鼠作實驗』,更不是『教我的老狗玩新把戲』。」
因此,我對崇拜禮儀的整個立場已經壓縮到只求劃一、恆久。我可以將就適應任何形式的崇拜,只要它不變就好了。但如果每當我開始習慣某一形式時,它就又改變了,那麼,我就很難在崇拜上有所長進,因為沒有機會經由「建立習慣」而更上層樓。
或者,那些革新,對我來說似乎只是品味問題,其實卻牽涉到重要的教義差別。但不可能全都如此吧!因為如果教義上的差別真的像崇拜儀式那樣差異繁多,我們可以下結論說:英國聖公會根本就不存在。無論如何,「禮儀煩燥症」並不是聖公會獨有的現象。曾聽過羅馬天主教徒也有類似的抱怨。
話說從頭,對教會的崇拜方式,我們平信徒該做的,是忍耐並努力善用。強烈偏好任何一種形式的禮儀,都是「試探」。為教會崇拜方式而分門結黨是我的大忌,如果能避免,可能就是在做一件很有益的事了!當牧者各持己見、「各人偏行己路」,消失於四面八方的地平線時,如果羊群仍忍耐相守、繼續鳴叫,是否最終會把牧人喚回?(英國歷代的戰爭中,有一些勝利不就是由士卒贏取的嗎?不是與將領無干嗎?)
編修公禱書
至於崇拜所使用的語言,問題則有些不同。如果你要一套使用本地話的禮儀,必然要是一套不斷變化的禮儀;否則,所謂本地化只是虛有其名罷了。「永不過時的英語」這個理想荒謬透頂。沒有一個現存的語言是永恆不變的;若有的話,你也可以要求河水停止川流。
如果可能的話,必要的改變,最好是逐步漸進地出現,而且對大部分人而言,是不動聲息的;這裡一點,那裡一點;一個世紀才淘汰一個過時的字,代之以新字──就如相繼問世的莎翁名劇版本中所改動的拼字一樣。情況是如此,我們也只能接受一本新的公禱書。
如果我們有資格(幸而本人福星高照,沒這資格)給公禱書的改編者一些建議,你會給他們什麼建議呢?我的建議恐怕不外乎一些沒有助益的警告:「小心,打蛋容易炒蛋難!」
在我們這支離破碎到不忍卒睹的教會中,禮儀中的語言──公禱書,是少數僅存的、維繫教會合一的元素之一。修改所帶來的好處務必要是巨大而確定的;否則,我們不應隨便把舊的丟棄。你能想像出一本新的公禱書,是不會造成教會分裂的嗎?
大部分力爭修編公禱書的人,都期望修改可以達到兩重目的:一是刷新語言,使其易懂,二是改進教義。這兩種手術都是痛苦的,也都是危險的,非得同時進行嗎?病人承受得起這樣的風險嗎?
新公禱書要添加哪些公認的教義?對那些教義的共識又能持續多久?我帶著惶恐問這問題。因為不久前曾讀到一則報導,有個人似乎主張把舊的公禱書中,一切不合正統弗洛伊德思想的東西都刪除。
編修語言的困難
刷新語言,應該為誰而改?一位我所認識的鄉村牧師問他的管堂,他對「忠誠且無區別地(indifferently)秉公行義」中的「無區別地」的了解是什麼?管堂回答說:「不對一個傢伙和另一個傢伙有差別待遇。」。牧師繼續問:「如果把『無區別地』(indifferently)這字改成『不偏袒地』(impartially),那你又如何了解?」。管堂回答說:「不知道,從來沒聽過那個字。」。
這是一個例子,試圖改變語言,希望更容易明白其意思。但這改變對那些受過教育的人來說,毫無意義,因為他們早已明白「無區別地」(indifferently)是什麼意思;但對那些未受過教育的人來說,同樣毫無意義,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不偏袒地」(impartially),這改變只能幫助會眾中,介於兩者之間的人,而他們可能只是少數分子。但願那些修改者在開始工作之前,先作好準備工夫,進行長期、實地的資料搜集,以及有關日常生活用語的研究,而不是單憑我們先入為主的假設。有多少學者知道,當不曾受過教育的人說「非個人的、非位格的」(impersonal)時,其實意思是「非軀體的」(incorporeal)?
另外,古舊但還不至於令人費解的字詞應如何處理呢?如“Be ye lift up.”,我發覺人們對古字詞的反應差異甚大。有人很討厭這些詞句,認為它們令所要表達的意思顯得不真實;不一定是更有學問的另一些人,則覺得這些古字詞給人一種極神聖的感覺,能激起人的虔敬之情。我們不可能同時討好這兩種人。
修訂公禱書的時機
我明白修訂公禱書是必須的,問題在什麼時候是對的時機。依我想,當兩種狀況出現時就表示時機成熟了。第一是「合一感」:當全體教會,而不是得勢的小眾,都覺得需要一本新的公禱書以表達其共同的心聲。第二是「人才的出現」:有這樣的人出現,他們有極佳的文學表達能力,能創作出好禱文。這需要一種特殊的寫作才能,不僅僅是好而已,而且是一種獨特的好,以致他們寫的禱文能經得起反覆誦讀而仍感人至深。克藍麥在神學上或有不足,但他所寫的禱文,可以打敗他的眾多前輩和所有現代人。要說改寫時機,我提的兩種狀況都尚未出現。
若不大改,作些修補或許是可行的。就我個人而言,我將十分樂意見到「你們的光也要這樣照在人前」這句話從捐獻的禱文中被刪除。在那情境下,這句話好像是勸勉我們在奉獻時,要故意叫人看見。
你提到麥考莉所寫《最親愛的珍》,我本想作點回應,但等下週再說吧。